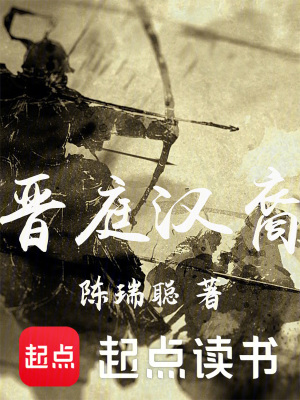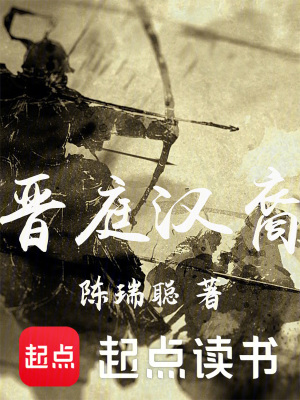
晋庭汉裔
陈瑞聪 著
类别:历史军事 状态:连载中 总点击:100 总字数:701729
频频回顾的是山峰,念念不忘的是大海。当姜维战死于成都大火的那一天,大汉帝国的余晖彻底消散了。 晋人站在他的尸体旁,挑出了一个斗大的苦胆,他们面面相觑。西晋帝国因这场胜利而建立,但未来将通往何方,答案却是惨痛的,四十年后,遍地哀鸿,九州涂炭,尸骨累累,饿殍如云。 在这场末世般的混乱中,因为责任与命运,刘备的曾孙,土生土长的安乐公世子,刘羡,踏上了复国之旅,他追寻着老师与大汉先祖们的事迹,与曹操、孙权、陆逊、卢植、荀彧……等宿敌世交们的子孙们再次相遇,然后,他在政斗与战乱中砥砺,蜕变,飞跃。 起初,他孤身一人,再回首时,他众望所归。
https://www.bok360.cc/book/1892492418120007680.html
写给读者的话
www.bok360.cc
其实按照传统来说,作为一名作者,应该尽量少在作品正文之外现身。但在网络文学这个大环境中,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是这样的近,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每天的焦虑,作者可以察觉到读者每天的悲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故作作者的矜持,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最前面,我想和这本书的读者们多说一些。
我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网文作者,我对这点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因为我写不了一般意义上的网文。传统意义上的网文是要给大家带来娱乐,让大家能充分代入进来,笑得开心,爽得畅快,没有任何忧虑,简单,纯粹。但我写不了这种文章,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理由,不是瞧不起,看不上,写不了就是写不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这样痛快的人。
写作无论多么想服务读者,归根到底还是作者写的,我只能写我写得出来的作品,只能写我想看的作品,而我的审美恰好有点奇怪。
在我的上一本作品《季汉彰武》里,我试图在我的笔下创作一个纯粹的圣人角色,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两百万字,我很满意,但成绩比较惨淡。我个人并不后悔,因为创作这样一个角色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来的一个执念,哪怕一个读者都没有,我也会写下去。但在写完后,一个新的问题就诞生了,接下来我该写什么呢?
没了执念,我就想写一点我自己喜欢的,又不那么私人化的文字。但这个范围有点太广泛了,很难化作一个完整的小说命题,所以我一度陷入纠结中。
有一天,我在刷知乎的时候,突然刷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晋八王之乱后,江东有东吴势力试图复国,而蜀汉没有?是否说明蜀汉的凝聚力是一种谎言?”提问者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蜀黑。作为一名大汉粉丝,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厘头,当时就准备写个三千字长文驳斥一下。
写着写着,我转念一想,如果把这个问题反转一下,写成一个小说的点子,应该很不错吧?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开始做准备,打算写个传统的穿越小说,附身到八王之乱时的安乐公身上,开始进行一个匡扶汉室。
随后我又感觉到了不对劲。到了这个时候,蜀汉相关的人基本都已经死光了,一个空降到安乐公身上的穿越者,他用自己的现代知识碾压古人,哪里能写出兴复汉室的感动呢?就算你强行往这方面煽动,也有些太刻意了。所以我打算做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主角定成土著。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历史网文写穿越者基本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了,你就算不是现代穿越者,也要是其余人来穿,比如李世民穿越刘禅啊,曹操穿越武大郎啊。这样写别人才会相信这个穿越者有能力去改变历史,改变世界。但我就想要那分原汁原味的情怀,相信我们当时的历史中自己就蕴含着改变的力量。
为此我需要说服读者,让大家相信这个土著有改变世界的力量,那我就必须要从出生时开始写起,让大家见证他的成长,见证他的飞跃。这种内容非常难写,也违背大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要追求这样一种英雄情怀,这是必不可少的。
但计划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故事虽然有情怀,有热爱,但是扑街的因素未免也太多了。但我确实觉得这么写很有价值,我也想写这样的故事,原因就像肯尼迪宣称要登月时说的那样:“我们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困难。”身为一名作者,如果对写作但凡还有一点爱好,就应该尽量把小说写得更好一些,而我觉得这样写确实很好。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书,算是我对于这个故事开始前的一点自白。如果点进来的朋友,你相信我们的民族肌体中流淌着英雄血脉,孕育着奇迹魂魄,那我写的就是英雄与奇迹,这将是很长的一段路途,可能会有不适与流泪的时刻,因为成就伟大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走到最高峰,愿你我一起共勉。
接下来就是一切的开始,姜维的死亡感动了天地(楔子二),上苍决定给安乐公一家一个孩子,一个新的机会(第一章),在快十年后……
楔子一 魏晋禅代
www.bok360.cc
汉朝的崩溃,并不仅仅是一场王朝的崩溃。
作为华夏大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大汉帝国的存在,改写了当时士人对现实的想象。
在汉高祖刘邦刚刚建立帝国的时候,无论是在野的野心家,还是朝堂上的功臣勋贵,包括汉高祖自己,谁也不知道帝国能存在多久,也许它会消失在汉高祖死后的一百年,也许它会消失于汉高祖死后的第二年,谁知道呢?人们只知道,这个帝国大概不会存在千秋万代。毕竟上一个号称要从始皇帝传承到万世的帝国,已经二世而亡了。
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国家啊!制度上,汉朝既有秦国锐意改革的郡县,又保有商周流传的分封,而皇帝御下持用的却是黄老之术;文化上,汉朝浸满了楚地浪漫奇幻的巫风,却又不失幽燕三晋的游侠习气,还时常有忠孝死节的儒门士子为民请命。
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些元素都格格不入,汉朝应该难以维持,但是它偏偏存在了下来,并且维持着这种微妙的平衡,历经了四代天子的交替。
当权柄交到汉武帝刘彻手上的时候,观望的人们渐渐反应过来:帝国并非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而是处在一个懵懂的童年,它的矛盾来源于它的幼稚,而它的多元也意味着它有无限的可能,而现在,帝国的童年即将结束了,因为酝酿的激情已无法再压抑,勃勃的生机将要突破障壁,伟大的历史正在喷涌而出,誓要把无限的可能化作为一种现实。
于是群英奋起,帝国北破匈奴,南平诸越,东取朝鲜,西开陇右,都护百国,又经昭宣之治,终于将大汉的历史谱写成旷古未有的华章。
中间虽然又经历王莽篡逆的波折,但光武帝再兴汉室,明章二帝励精图治,终于又在汉和帝手中恢复永元之隆的盛世图景。而不知不觉间,大汉帝国也已经存在三百年了。
三百年的岁月中,帝国已经改变了太多,分封制度已名存实亡,商鞅设计的二十等军功爵也沦面目全非,转而全面为察举制度所取代,而各地郡守察举出的孝廉、秀才,却常常令人大失所望。尚武精神正在衰退,忠孝之道又变得僵化虚伪,再伴随着不断的天灾与人祸,渐渐有人醒悟过来:帝国已经老迈了,再伟大的历史,也终究有结束的那一天。
但要大多数人们认清这一点,还要等到汉灵帝死后。
那一天,十常侍砍下了大将军何进的头颅,司隶校尉袁绍紧接着策划了一场屠杀,袁术同时在南宫九龙门肆意放火,烈焰腾空,甚至烧红了当夜的月亮。曹操、董卓、王允、卢植、刘备等人都目睹了这场壮观的洛阳大火,这场火焰将皇帝的权威尽数焚毁,并且拷问着天下所有人,接下来,你们将何去何从?
在这个残酷的真相面前,有的人选择篡权乱政,有的人选择以身殉国,有的人选择避世隐居,有的人选择另立门户,有的人选择,再一次拯救帝国。
也许是大汉的历史太过辉煌,也许是大部分人对未来感到迷茫,帝国在两个丞相手中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第一个丞相名叫曹操,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历史上曹操确实将皇帝迎至许都,并借助皇帝的大义,在血泊和尸堆中重新整合了北方。
但紧接着,两个问题摆在了曹操面前,第一个问题是政治意义上的,汉朝制度还能继续沿用下去吗?
第二个问题是事关个人命运的,他能够接受事后如霍光一样被清算,成为汉朝历史的注脚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曹操的回答是不能沿用。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曹操的回答是不愿被清算。
于是曹操背叛了早年自己的理想,成为了如王莽一般的汉贼。
曹操立国为魏,定都邺城,开创四征四镇、士家任子、九品中正等制度,这些制度真的能够解决汉朝面临的问题吗?曹操不知道,他在死前安慰自己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也就是期许后来子孙的智慧能够超越自己,再开创一个八百年之长的伟大王朝吧。
但很不幸,在曹操死后的第二十九年,太傅司马懿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在洛阳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政敌曹爽三族,并夺取了魏国的最高权力,这一幕与五十年前的袁氏兄弟纵火洛阳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此次既没有半路杀出的董卓,也甚少有为国死节的忠臣罢了。
当年迎合曹操取代汉室的士人们,如今又顺理成章地再迎合司马氏,其中甚至不乏曹魏皇室宗亲。汉室的神圣权威被取缔后,曹魏自己未能建立起同样伟大的叙事,反而进一步消解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为什么天子是天子?过去的历史中,只有一个大汉帝国,而这样的帝国,以后真的还会有吗?
第二个丞相名叫诸葛亮,起初,他只是一名避难在隆中的农夫,不想关注世事。但不知是因为被刘备三顾茅庐的真情所打动,还是因为对曹操篡汉自立的仇恨驱使,诸葛亮终究还是出山效命,为帝国在益州谋得了立足之地。
他同样面临着两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和曹操完全不同。
面对第一个问题,诸葛亮知道汉朝制度已经落后了,但他认为曹魏的制度更为败坏。
而面对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愿意。
作为将为历史铭记的圣人,诸葛亮饱含对大汉的热爱,他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将所有的才华、爱恨、心血都用在了延续大汉寿命的道途上。
虽然仅仅占据西南一隅,虽然屡经挫败,但他的品格注定彪炳千古,他的执着注定光耀千秋。
即使最后并没有成功复兴大汉,但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经让司马懿在对垒中黯然失色,也让帝国最后的尾声余韵悠长。
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继承了他的遗志。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们,也始终与帝国的命运抗争着,希望能在这场与岁月的赛跑中多赢得哪怕一分一秒。
司马懿冷峻地注视着这两个人的选择,对于他来说,过去不值得叹惋,更不值得缅怀,他知道未来一切都将毁灭的命运,但仍然要牢牢把握住这空悬的权柄。
曹操的猜疑早就让司马懿变得残忍,使得他不太记得大汉帝国光明的一面,反而开始享受权力斗争中的腥风血雨,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择手段地获取胜利。但是胜利的代价是什么?
当司马昭面对高贵乡公的尸体,他才隐约明悟一点,继而当街痛哭。
许多人说司马昭的痛哭流涕虚伪,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任何政治家都能从中嗅出一股残酷的味道,这种残酷是从袁术放的那把火开始的,这把火还在燃烧,它在平等地燃烧所有人,所有制度,所有品德,都在成为这把火的养料。
当天子能够死在洛阳的街道上,谁又能从中置身事外呢?
于是司马昭决定伐蜀,不顾一切地伐蜀,他要用大汉帝国最后的余晖,来挽回这场即将失控的灾难。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钟会围攻剑阁,邓艾偷渡阴平,都成了姜维的注脚。在他那惊天动地的一死后,蜀汉终于画上了句号。
好在蜀汉终于灭亡了,司马昭借助伐蜀大功,成功晋位晋王,后其子司马炎代魏。虽然名义上,晋朝的天命来自于魏帝禅让,但是私底下,也有很多士人流传说,晋虽受魏禅,实承汉统。而司马炎称帝以来,也大肆追褒诸葛亮,希望能够以此挽回人心,重塑国格。
蜀汉即灭,东吴胆寒,看起来,又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即将诞生了。
正如当年汉朝的诞生一样,这个帝国充斥着各种各样奇怪的人群与制度:既有二十等军功爵,也有九品中正;既有士家世兵,也有募兵部曲;既有三千死士,又有孝廉儒生……
但它与大汉帝国也有极大的不同,那就是人们看不见热爱与希望。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大家都没有可以相信并托付生命的信念,只能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五石散,以此来排解满腔的失望与怒火。
汉朝崩溃了,但崩溃的不仅仅只有汉朝。
伟大的时代结束了,眼下灾难还未降临,布满疮痍的大地上遍布着大汉帝国的废墟。而后人们穿行其中,一面听着英雄的传说,一面迷茫地选择自己的归宿。或许一切都结束了,或许还没有结束,但大汉曾流传有这样一句古话:死灰犹可复燃。
在废墟的角落里,仍有火种在等待积蓄。
楔子二 成都大火
www.bok360.cc
“大将军,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张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四面八方都传出了喊杀声,仿佛怒涛一般此起彼伏,不见停息。周围的火光已经汇聚成海,炙热的焰浪正在屋檐间流窜沸腾,令这原本漆黑的夜晚亮如白昼。纵使身处暗室之中,光芒还是透过窗户的竹帘照进来,把屋中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宛如长蛇,在墙壁上不断舞动。
姜维看了张翼一眼,布满血丝的双眼正映照着远处的火光,仿佛流萤一样跃动。他的表情耐人寻味,糅合了疲惫和深切的悲悯。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叹息着说:“我知道。”
“大将军,接下来?”句扶睁着仅剩的一只眼睛,斜绕过前额的巾布浸透血水,混合了冷汗,沿黑乎乎的面颊划出几道浅纹。
姜维苦涩地想到,是啊,即使已经身处绝境,但自己仍然是大汉的大将军。在最后的希望覆灭前,在最后一个汉卒战死以前,自己都没有理由放弃,因为,这是三十五年前,老师对自己的期待。
在回想的这一个瞬间,姜维似乎从老年回到了青年,计败的沮丧也被一种坦然所取代。他挺直了身子,缓慢而又坚定地说道:“得有人冲出去,把城外的军队带走。”
“难道还有机会?”蒋斌出声问道,很显然,他并不理解这个命令,或者说,他不知道希望在何处。
“没有机会。”姜维朝地上啐一口含血的唾沫,再继续解释说:“但只要有人活下去,总有机会。”
说罢,姜维把腰间的佩剑缓缓抽出,残缺的剑锋与剑鞘摩擦出呲呲的噪音,但却似乎含有神奇的力量,令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看着年迈的大将军在黑暗中擦剑。这柄宝剑是天子御赐的章武剑,已陪伴了姜维三十多年,姜维曾用它无数次来发号施令,但在刚刚,它才第一次染上鲜血,而后砍断了四个人的头颅,多了四道缺口,故而姜维擦剑时格外专注和细腻。
看着大将军斑白的头发,眉眼间的细纹,部从们都默然了。眼前的这个老人,自二十八岁入蜀以来,整日忙于军务,至今未婚,更没有儿女,生平所得钱财从来都分发给蜀中百姓,对他来说,对错或许难以评判,但品德却无可指摘。可这样一个人,今日就要葬身于此了吗?
忽然,数支箭唿哨而来,立刻击碎竹帘,牢牢钉在身后的土墙上。光芒和热浪随风而入,照亮了众人的面庞,魏兵的叫骂声接连涌入,让他们快快出门投降受死,但房中众人仍岿然不动。
姜维扫视着部从们的神情。这里还跟随着他的,基本都是老将了,皮肤上的皱纹多如狄道山径中风蚀的枯石,周身负伤,心力交瘁,杀气腾腾。但其中还有三个年轻人,恐惧通过表情和动作表露无遗:他们第一次离死亡如此接近,腿脚和瞳孔都在止不住地发抖。
那是渴望希望的神情。即使身处绝境之中,这些年轻人还是本能地想要活下去,可是年轻的尊严又使他们拒绝接纳这种软弱,故而双眼时而如山泉清澈,时而如落叶萧瑟。姜维熟悉这种神情,如今的他也喜欢这种神情,他相信这是通向伟大的必经之路。
于是姜维将他们三人点名出列,嘱咐道:“等会我们出去,你们三个往西走,别回头,一定要活着赶到军营。”
这突然的命令让年轻人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大将军的深意,却能够听出话语中包含的沉重意味:大将军已经决心赴死了,为了他们能活下去。三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解脱,紧接着又产生一种耻辱,因为真正的勇士是不需要靠他人来活命的。这耻辱迫使年轻人拒绝,可一看见大将军瞳孔的火光,他们就通通哑住了。
最终,一个年轻人艰难地问道:“大将军,那之后呢?”
“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等待。”姜维注视着他们说:“竭尽所能地等待。”
等待什么?等待多久?年轻人还想再问,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房外的魏军正在渐渐靠近,其中还掺杂着马蹄声和呼啸声。姜维看了三人一眼,立刻带领其余人走了出去。
他以坚定不移的脚步,穿过断壁残垣的阴影,而后立定了。在炽热亮眼的火光下,姜维一手持章武剑,一手负于背后,仿佛天神一般睥睨着眼前成千上万的魏兵。在他的身边,是十六个陪伴他征战数十年的老战友,而在他的背后,是正熊熊燃烧的成都锦宫,火焰已经烧红了月亮,而硝烟也接天连夜,继而在上空堆聚无数乌云,似乎随时会沉沉压下。
这样庄严的景象吓住了包围他的魏兵们,他们听说过张飞扼守断桥喝退千军的传说,但亲眼见到还是第一次。这使得他们生出一种震撼,不约而同地从箭囊中抽出箭矢,然后搭上弓弦,将角弓拉如满月。但不知为何,魏兵们没有立刻松开弓弦,是没有勇气?还是心生敬意?不论如何,火焰中所有人都安静了。
他们听见一个老人在呐喊:“汉大将军姜维在此,尔等速来决死!”
魏卒以一阵如期而至的箭雨作为回应。
就这样,十七名老兵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战斗。这种战斗,既不是为着胜利,也不是为着突围,而是受一个十分单纯的愿望所支配,就是要在自己倒下之前多杀死一个或几个敌人,死不投降。
魏卒如同潮水般涌向汉军,厮杀声再次响起,但这已无关胜负,无关示威,只是人们需要呐喊,需要证明自己还存在。而上苍也在此时做出了回应,撒下春日蒙蒙的雨丝,缠绕在双方的甲衣与刀锋上。
廖化和句扶都近乎残废,很快就倒在魏兵组成的黑流中。而张翼一直跟在姜维的身边,负了十几处伤,一时流血过多,栽倒在地上,失了知觉。过了片刻,他突然抬起头,睁开血红的眼睛,但是他没有看见大将军姜维。正在这时,有一群人从他的面前奔过。他从地上捡起短剑,用力向敌人掷去,恰好刺中了一个魏兵的头部。魏兵大叫一声,横倒在地上。“又赚了一个!”张翼在喉咙里骂了一句,倒下去死了。
姜维已经受了四处箭伤和六处刀伤。他的身边还剩下赵统、蒋斌、关彝三人,而且都负伤了。他们四个人杀到一处小丘上,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敌军。有一个穿红甲的敌将带着一拨人乱箭射来。姜维的左胸上又中了一箭。他拔出箭,大喝一声,从小丘一跃而起,竟杀到敌将的面前,满是缺口的章武剑又一次砍中目标的脖颈。但这一次,敌人的头颅没有落下,只是伴随着“呲”的一声,姜维手中的重量一轻,大量的鲜血飞溅到脸上,而剑锋已断为两截。
雨势变大了,雨水滴滴答答地敲打在泥土上,尸体上,还有火焰上。又有狂风袭来,周遭刚刚吐绿的树梢随之簌簌作响,火势也随之明明灭灭。最后是一道春雷,白光过后,霹雳一声炸裂在众人头顶。
这一声打醒了姜维,他仿佛接受到了某种预兆,知道自己快死了。此时他老迈的身躯上满是血水,他的每一寸肌肉都在呻吟。可他仍然挥舞着断剑砍杀,并呼喊着下边的话,鼓励着他仅剩的将士,也回应着上苍正注视着他的魂灵:
“先烈在上,勇士捐躯!苍天犹在,大汉不亡!杀!杀!”
他的背上又中了一刀,身子猛一摇晃,几乎要摔倒在地。但姜维赶快用左手撑住地面,回身砍死了一个敌人。直到此时,他终于发现,汉军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但真的是一个人吗?恍惚间,姜维看见了数之不尽的魂灵,他们就站在他的身旁,默默注视着他,为首的是一个熟悉的早已死去多时的面孔,正微笑着朝他颔首。
错觉只存在了一瞬间,很快又如潮水般消散,那些魂灵瞬间变回了昏暗中残忍的魏兵。他们围成一圈,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个濒死的老人。有人说,要他投降。他感到很耻辱,站直了身子,很愤怒地说:“堂堂大汉,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但声音已经很弱,很低,不能连贯。
片刻之间,他的胸口又连中两剑,一剑刺穿了肺,一剑刺中了心室。这终于使他倒了下去,在泥水里,断剑也扔落地上,旁边是一团还没有熄灭的篝火。他的耳膜还响着刀剑声和喊杀声,而他自己像做梦一样,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仍在战斗,仍在呼喊。不过,他又模糊地知道自己受了重伤,倒在地上,血正在向外奔流。
年轻人逃出去了吗?姜维的脑海中刚闪过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念头,但很快又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大汉真的亡了吗?不甘驱使着姜维挣扎,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许下一个愿望,然后哼了一声,彻底失去了知觉。
黑暗的苍穹交织着白光,爆发出潮水般的雷鸣,雨水滂沱而下,将鲜血与灰烬都冲刷入江流,徒留下一片焦黑的废墟。人们纷纷为这种景象所惊异,私下议论说:这个季节,按理是有春雷的,但大风大雷的天气,还是非常罕见,莫非是姜维的魂魄化为厉鬼,在天上作怪吗?
于是有人好奇地剖开姜维胸膛,从满腔鲜血中取出了一颗如斗大的苦胆。魏卒面面相觑,觉得坐实了方才的谣言,然后小心翼翼地踩碎了这颗胆囊。
夜晚结束了,浓云散去,朝阳重生,新的一天继续开始。众人把那一天作为新帝国的起点,在第二年改元泰始,意为太平自此重新开始。然后开始重建锦官城,他们在骨殖上铭刻墓碑,在废墟上夯实土墙,在灰烬上遍植桑树,在城野中迁来流民。然后断剑销为尘灰,墓碑攀上苔藓,再也不见当时血战的踪迹。
https://www.bok360.cc/book/18924924181200076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