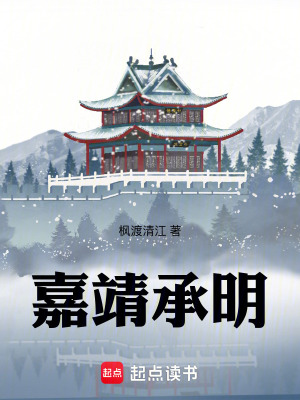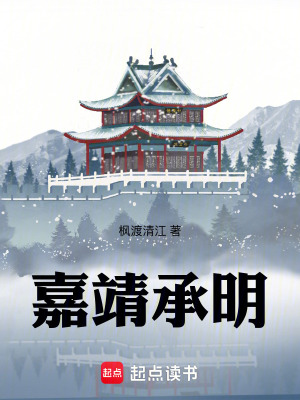
嘉靖承明
枫渡清江 著
类别:历史军事 状态:连载中 总点击:100 总字数:1555000
正德十六年春,皇帝朱厚照驾崩,大明的国运来到了十字路口。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喜正德朝强军事而损民生的改革,志在裁减冗员、以牺牲军事实力的方式与民休息,还希望继承大统的嘉靖帝朱厚熜能重现弘治光景。 但来自后世的朱厚熜对此不以为然,且有他自己的打算。当他决定把历史上嘉靖帝的才智,学来用在治国安民和实业发展而不是中途放弃改革转而修仙求神后,汉文明就真的迎来了他的中兴之世,不但国强亦民富,君德更是惠及宇内。 于是,那句 “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民间俚语,便成了 “嘉靖嘉靖,家家皆景”。
https://www.bok360.cc/book/1892430578383953920.html
第一章 兴王世子
www.bok360.cc
大明湖广布政司兴王府。
世子朱厚熜背着手,从王府中正斋里,走了出来,逡巡着午后的王府。
接着。
他不禁嘴角微扬。
因为他昨日已从长史袁宗皋口中得知,当今皇帝确已经病重。
这意味着,他真的要成为下一任皇帝。
即历史上的嘉靖皇帝。
不过,现在的朱厚熜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嘉靖皇帝,而是一来自后世的穿越者。
朱厚熜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成了大明朝正德朝的一婴儿,而且还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嘉靖皇帝朱厚熜。
但经过了这么些年,他也渐渐接受了自己是朱厚熜的现实。
且在这些年里,他早已开始期待着,将来成为嘉靖皇帝的一天。
朱厚熜知道,眼下的明帝国,在正德皇帝的一番军事改革后,军事实力倒是提升不少。
但是伴随着的却是军事开支增加的同时,也造成明帝国在财政上面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民生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
甚至在正德十五年,连富庶的淮扬地区,都因为赈灾不力,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
湖广也因为这些年来公共建设不足,在旱灾水灾相继来袭时,也造成大面积地区受灾,饥荒蔓延到十五府。
而当今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对这种情况自然非常不满。
因为正德的军事改革,一方面导致文官地位下降严重,一方面也的确导致天下民众更加困苦。
所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清流文官们很迫切地希望新皇帝能支持他们裁减军额军需、节省开支,纾民解困,同时提升文官的尊严和权威。
但朱厚熜不认为大明要保证民生就必须要牺牲军事实力。
他希望他当上皇帝后,能够让大明帝国能够在国强的同时,也能民富。
朱厚熜也希望他当皇帝后,能够让大明的嘉靖王朝更好。
而现在,于操权方面,他就得先向历史上的嘉靖学习。
因为无论是做最利己的事,还是做最利他的事,皆需要大权在握,才能做事,不然都会寸步难行。
朱厚熜现在只好奇,自己要是在学着嘉靖操权的同时,把能够彻底掌控整个明帝国的权术手段用在国强民富的大业上,到底会让中华文明产生多大的正面效应?
而因为要学着嘉靖操权,所以朱厚熜自穿越后到现在,没有表现出半点穿越者的特质。
他一直在韬光养晦。
尽量让外界不知道他是一个暗藏雄心的少年。
何况,在他没有明确收到是让他继承大位的遗诏之前,他也不敢确定,他如果过早的锋芒毕露,会不会导致他最终会和皇帝大位失之交臂。
毕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
南宋权臣史弥远就因为太子赵竑过早表现出要除掉他的态度,而在其成为皇帝之前将其废掉。
虽说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很难再有史弥远这样的权臣,但谁也说不准,会不会有人因为他过早展露出不让人喜欢的政治态度,而宁肯冒着别的风险,也要让他做不成皇帝。
总之。
只有他拿到正德皇帝正式让他继承大位的遗诏,他才真的在并非铁板一块的统治阶层内部,具有拉拢一部分贵胄官僚为自己基本盘,承认自己是君主的资格!
而眼下能决定朱厚熜是否顺利成为皇帝的人物就是杨廷和。
这个因为是正德老师而受正德敬重,又承弘治遗泽,在后宫和士大夫群体中颇有声望的内阁首辅。
偏偏杨廷和还是以理学为信仰的保守党。
所以,这些年,朱厚熜和历史上的嘉靖一样,表现的很低调,甚至刻意做出一些迷惑杨廷和和他的拥趸者的行为。
为此。
他从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后,就一直在王府内认真学习程朱理学,严守程朱理学要求的礼仪规范。
后来。
他更是常常接济贫困士子,兴办义学,勤俭持家。
除此之外。
朱厚熜甚至还以朱子撰文写诗以立言,在日常生活中也刻意伪装得很节俭,明面上每日只餐两顿,且每顿不超过三个菜,四季常服也只做八套。
而见外人时,他里面更是只穿布衣。
如此一来。
天下人皆知他笃学礼士,宽厚勤俭。
正因为朱厚熜表现的礼儒崇理,再加上他又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宗藩,所以文官们让他兴王府的禄米也被拖欠扣留的很严重,甚至比别的宗藩还要严重。
因为按照大明的财政制度,在宗藩禄米发放这块,一直都是由地方文官直接从税收存留中直接拨付于当地宗室。
甚至,禄米是本色拨付即拨粮食,还是折色拨付如折银折钞,都是由地方文官们确定,然后奏请皇帝同意。
具体而言,就是地方文官在地方收上税粮后,税粮会被分成起运和存留两部分,起运的部分会运抵京师各仓,而存留的部分,则用来发宗藩禄米和官俸以及生员廪食等。
也就是说,宗室禄米的发放权力在地方文官们手里。
而一般情况下,地方文官们会根据境内宗藩好不好惹,来决定是拖欠禄米发放以索贿,还是足额准时发放禄米,或者说找别的借口直接不发。
自然。
藩王越是仁厚要名,被拖欠的禄米自然就会越严重。
藩王越是蛮横不要脸敢闹事甚至不惜把官司打到皇帝面前,文官们反而越不敢拖欠,皇帝也越不敢因为一点禄米担下一个苛待宗室的名声。
而朱厚璁现在既然要立仁厚礼士的人设,自然也就被文官以各种借口拖欠或扣留部分禄米乃至全部禄米。
借口也好找。
无非是受灾严重,逋赋严重,所以没有多少存留,而仅有的存留也只能拿来先赈灾。
地方宗藩没有权力干预地方行政,自然也不能查账确认。
好在朱厚熜的兴王藩传到他这里才两代。
人口也就不多。
即便禄米被欠发扣留,但有历年积蓄与赐田的收益在,倒也支撑得住。
但自己的禄米被扣发被贪墨,自己还不能伸张,还得对这些扣发贪墨自己禄米的文官礼敬对待,对于朱厚熜而言,还是很憋屈的。
凭什么好人就该被拿枪指着?
但就在袁宗皋告诉朱厚熜,说正德帝确已病重后不久的次日,也就是今天,湖广副使王涎就送来了欠发给兴王府的禄米。
朱厚熜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按照朱元璋规定的继承皇位规则,无嗣的正德皇帝一旦去世,他就是继承皇位可能性最大的宗室。
而地方文官们自然担心他这个贤王,会不会在当皇帝后,因这事记仇,而卡他们的仕途。
尽管他这个贤王为了贤名可能不会明着逼他们补足欠发的禄米,但谁知道会不会暗地里阻止他们进步。
所以,这个时候的湖广地方文官也就不敢再欠发他的禄米。
王綖送来欠发的禄米,朱厚熜自然照例要亲自设宴感谢一下。
于是,他也就在这日午后,从昔日自己读书学习的中正斋中走了出来,准备去承运门见王綖。
兴王府和紫禁城的布局类似,有内廷外朝之分。
而承运门就是外朝正门。
朱厚熜一般就在这里见外官。
当朱厚熜来到承运门后,王綖当即大拜在地,诚惶诚恐地道:“臣叩见世子!”
大明宫廷素来没有秘密可言,如同筛子一样。
既然朱厚熜都知道了正德皇帝病重的消息,那王綖这种握有地方实权又奉杨廷和命暗中盯紧兴王府动态的兵备道官员,自然也早就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了正德皇帝病重的消息。
但王綖没想到,不到半年,正德皇帝就真的会在落水后越发病重,使得自己恩师杨廷和开始向自己询问兴王世子情况,而让兴王世子朱厚熜这么一个本来不会被人重视的宗室子弟,有了成为下一代天子的可能。
所以,王綖现在是真担心朱厚熜会记恨他们这些湖广官员欠发兴王府禄米,也害怕自己现在的半点不敬,就会让很可能成为大明天子的朱厚熜心生不满,便在朱厚熜面前表现的非常恭敬。
第二章 当为圣天子
www.bok360.cc
“兵宪请起!”
朱厚熜在见到王綖跪在自己面前后,就微微笑着,伸出了手。
依旧表现的非常礼贤下士。
王綖听到朱厚熜声音亲和地对自己说了个“请”字后,也不禁内心很感动。
这让他不由得承认,当今兴王世子的确待自己这些文官仁厚亲切,无疑是值得做下一任天子的。
王綖道谢后,就一脸愧怍地奏禀说:
“因去年一场大水,所以田赋征收着实不易,另藩库存粮也先用到了赈灾上面,也就短了兴国禄米未发,好不容易才从未受灾的几个县,调运了一批存银,为禄米折色,特敬发于国。”
“但终归是臣等无能,而未能及时发足禄米,使世子与国中诸贵人受了委屈,实在有罪!”
王綖继续说后就向朱厚熜再次一拜。
朱厚熜再次请王綖起身后就笑着说:“去年湖广十五州府皆成泽国,安陆也未能幸免,我是知道的,幸而有卿等忠廉之臣牧守湖广,才使得大灾之后无大变,我感念诸卿赈灾及时、牧民有方还来不及,怎会因为禄米欠发而怪罪于卿等呢?”
“何况,母妃与我皆崇尚节俭,所以国中用度素来不大,即便一时禄米停发,乃至赐田因灾无收,但靠旧年积蓄,也还能支撑,比不得庶民卖儿鬻女之难。”
对于朱厚熜而言,他是乐于见到王綖来向自己补发禄米的。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王綖还是想进步的。
朱厚熜认为,只要一个人还想进步就好。
只要想进步,就能拿捏。
他甚至还怕王綖不想进步,只想躺平,而不提前补发禄米。
那样的话。
他还真拿王綖没有办法。
毕竟王綖欠发兴王府禄米的理由是为了先拿粮赈济灾民。
他自然不能说王綖先拿粮赈济灾民不对,也不能将来就要因此把王綖处死。
不过,王綖现在把禄米折银补发给他,他自然也不会拒绝。
因为这笔款在赈灾结束后,只会被留在地方藩库里,而被贪官墨吏慢慢漂没掉。
与其如此,朱厚熜还不如自己收下来。
何况,他现在也很需要银子。
须知,他这十四年来,由于要立一个重义轻利的儒家君子人设,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开源手段,自然也没怎么增加财富。
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钱的。
朱厚熜也就没有拒绝收禄米。
而朱厚熜这么说后,王綖也忙一脸感激涕零地躬身一拜:“世子宽仁爱民,臣铭感五内!”
朱厚熜只是淡淡一笑,而看向左长史袁宗皋说:“兵宪运禄米来辛苦,赐兵宪宴于卿云门,还请先生作陪,以全国朝亲亲之谊。”
袁宗皋拱手称是。
王綖这里也忙谢了恩,且在看见朱厚熜袍服下的布襟后,怔了一会儿,暗叹这兴王世子果然节俭。
接下来,朱厚熜就暂时离开了承运门,回了中正斋。
中正斋是朱厚熜目前读书之所,在寝宫卿云宫之北。
而卿云门则在卿云宫之南,是朱厚熜历来宴请朝廷官员的地方。
所以,王綖在接下来就跟着袁宗皋来到了卿云门。
等他们来到卿云门时,卿云门内,已摆好了宴席。
而王綖就因此看见,整个席面上,燕窝鹿尾、鱼翅海参皆有,便向袁宗皋拱手说:“请公告知世子,国中赐宴实则太奢,臣不当消受!”
袁宗皋则笑着说:“我们世子说,公等皆是国士,礼当如此,非只待公这样。”
王綖听后非常感动,嘴角抽动,而不禁望北而叩:“世子礼士如此,臣唯有勠力为国,方可报答!”
接着,王綖也就还是入了席,与袁宗皋东西对坐。
恰好。
黄锦在这时带着提着食盒的王府内官,刚好路过卿云门,且说了一句:“快点,世子爷到现在都还没用膳,早饿着了!”
王綖听到了黄锦这话,因想到杨廷和的嘱咐,便放下筷子,走了过来,拦住黄锦,拱手一拜,问道:“敢问公公,世子餔食(晚餐)怎样?”
黄锦便让人打开了食盒给王綖看。
俄然。
王綖就见食盒内就野菜豆腐汤一碗,稀粥一碗。
“世子怎吃的如此清简?!”
王綖大为惊讶地问了起来。
黄锦则笑着回答说:“我们世子爷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眼下安陆灾民遍野,多食野菜啃树皮之辈,身为世子,他自当与民同苦,然后方知民生之难,知祖宗之德,故决定孝期餔食茹素,而以野菜和豆腐为主。”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王綖听后喃喃念起了这句出自清朝理学大儒朱柏庐《朱子家训》的话,而接下来则是久久不言,且半晌后,只红着两眼到了席上,而对席上的袁宗皋说:
“世子果然深得理学之教,大有俭朴仁爱之德,令人钦佩!”
袁宗皋笑着颔首说:“世子素来敬重王公的为人,如今能得王公此言,必当大悦!”
“鄙人不敢当世子如此看待。”
王綖则拱手回了一句,且不禁哽咽着说:
“虽说尊者赐,不当辞,但臣怎能一边坐视世子茹素食野一边在这里食肉尝荤,故请长史转告世子,此宴,臣万不敢再受用!”
“也罢!”
“其实世子早知公忠介,不喜铺张,故早已有命,若公辞宴,便将此宴所有菜肴皆赐予义学,令义学中孤幼食之。”
“既然公不肯受用,我便奉世子命,令人将此宴席撤去。”
袁宗皋叹了一口气,且说了起来。
王綖听后更加感动,不由得再次一拜:“如此更好!”
随后不久,王綖就来了朱厚熜这里,准备拜辞朱厚熜。
而他因此,得以亲眼见到,朱厚熜甘之如饴地就着野菜豆腐喝粥的场景,并不禁热泪盈眶,且在回衙署后,就立即给杨廷和写了信:
“恩辅谨启,兴世子确如传闻所言,不但礼待士大夫,还俭朴至极,餔食竟以野菜豆腐佐粥食之,且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可见深谙圣贤之道,勘为圣天子也!”
王綖写完信后,就将信交给了自己的心腹:
“立即急递送京!”
“是!”
接着,王綖就满怀期待地走出屋子,颇有兴致地于中庭信步起来,而望着一轮皎月,嘴角微翘地自言自语道:
“苍天佑我士林,皇明将重现弘治之世也!”
不过,王綖不知道的是,朱厚熜在他感叹弘治之世将再现时,正于寝宫内喝着奶子。
对于才十四岁的朱厚熜而言,他可不想让自己因为目前要立节俭人设而营养不良,进而影响自己的生长发育,所以,他每晚睡前基本上都会喝一碗热奶子。
不过,这件事,自然只有王府里与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而朱厚熜在喝完热奶后,就在长史袁宗皋和伴读黄锦的陪同下,来了王府广充库,对王綖送来的禄米折色进行过目。
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国,财权的把控很重要。
历史上的嘉靖帝就一直在财权未肯有半点松懈,甚至后世有人称他是嘉靖朝真正的户部尚书。
朱厚熜既然立志要在权力的路上学习嘉靖,自然也不会在财权上有半点松懈。
所以,王府的每进一笔收入,他都得过目,且在开支上自己拿主意。
另外,不久前,正德已下旨,让他以嗣子暂管府事,因而,即便他现在年纪不大,但王府大事已经是他说了算。
且说,王綖这次一共给兴王府补发了五万两银子的禄米折色,算是基本补齐了安陆州历年欠发兴王府的所有禄米。
而价值五万两的大银锭皆是亮白如雪,堆叠在一起,也的确很晃人眼。
朱厚熜的瞳孔也为之铮亮许多,嘴角微微勾起弧度。
朕的钱!
皆是朕的钱!
虽然只是五万两白银,但在这个百姓一年开支不过五六两的时代,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不过,朱厚熜明面上倒是很镇定,也没有真的把心里的话明着喊出来。
毕竟他现在还不是天子,还不能直接以朕自称,也不能表现的太爱财。
第三章 会是好皇帝吗?
www.bok360.cc
朱厚熜只背起手来,点了点头,像他前世下街道社区视察时一样,只对袁宗皋说:
“既然历年未发禄米皆已补发齐全,而现在王府用度也有限,且去年一场大灾让安陆州几成泽国,国中佃户都受损不轻。”
“那便下王谕,今年佃租减半!且从明年开始,国中佃租永减一成。”
袁宗皋和在场王府文武官属皆喜形于色。
按明制。
王府文官,包括长史,皆选自本地士子。
而武官自不必说,都是就藩时就跟随王府的锦衣卫子弟。
故而,王府赐田的佃农其实很多都是王府文武官员的亲友在佃租王府赐田,然后再把佃租的田进一步租佃给无地百姓。
而佃租王府赐田的文武官员们的亲友们,用后世租房的方式来比拟,就相当于二房东。
这也是为什么藩王府的官员爪牙们历来收租很积极,不惜打死佃农的原因。
朱厚熜现在减少佃租,本质上也只是让利于王府的官员和世袭护卫们,而并不能直接惠及到耕种王府田地的百姓身上。
所以,袁宗皋等藩王府文武官员们才都喜不自胜,而不是真的因为朱厚熜让利于百姓而为百姓高兴。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朱厚熜要保证自己王府的人对自己足够忠心,进而使其成为自己将来掌控天下的基本盘核心,让他们为自己的帝王路产生价值,就得先示恩于他们。
让他们知道,他这个世子得了好处后,是不会让自己人吃亏的。
人主可以刻薄,但不能寡恩。
朱厚熜也知道历史上的嘉靖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他的老师袁宗皋还是奶兄弟陆炳,都因此在数年位至显贵。
而正因为历史上的嘉靖这样做了,所以陆炳才会在嘉靖寝居之处被烧时,不惜冲入火海将嘉靖背出来。
须知,十步之内无皇权,身边人的恩典要是不给足,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他现在减佃租就是一种名为让利百姓,彰显贤名,实为拉拢身边人的经济手段。
这样他既会让身边人满意,也会让外界觉得他是真的爱民如子,不会觉得他只知照顾身边人。
朱厚熜在这么吩咐后,喜形于色的王府官员们因而越发地期盼他能成为未来的大明天子。
在他们看来。
朱厚熜现在还是兴王世子都愿意主动降恩于他们,若是做了皇帝,只怕会降更大的恩德。
袁宗皋作为年过花甲的长者,还能在明面上显出淡然之态,除浓眉微展外,面色上倒无其他变化。
但作为王府伴读、侍卫的陆松与黄锦等中年官将已不由得抿紧了嘴唇,对未来眸露期待之色。
不过,还是朱厚熜身边一校尉的奶兄弟陆炳倒是因为年少单纯,只对朱厚熜眸露敬佩之色,而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这位如同兄长一样的世子爷是真的爱民如子,将来真要是做皇帝,那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皇帝。
……
“兴世子会是一位好皇帝吗?”
京师。
杨廷和此时正于庭中仰望苍穹,喃喃自语了一句。
由于正德皇帝已处于弥留之际,所以到了需要考虑下一代天子的时候。
正如近日刑部员外郎周时望在奏疏中的话说:“圣体违和,辍朝累月,天象变异,人心忧皇。乞念宗庙社稷之重,建立国本以杜邪谋。”
言外之意就是劝正德早选宗室子而立为皇嗣。
但内阁首辅杨廷和还没有做好决定请旨选宗室子为正德皇嗣,所以对这些请定国本的奏疏皆未票拟上报。
因为杨廷和不想下一代天子继正德之嗣!
那样的话,下一代天子就会与正德皇帝有父子之名。
既然有父子之名,按照三年不改父之制的儒家孝道,那新天子要改正德时的制度就会很难,就会失去道统。
而杨廷和又早已不满正德朝重用内宦和武将的制度久矣,恨不能即刻就改掉此政,重新恢复文官的尊崇地位。
当然,北宋时期,神宗驾崩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倒是以母改子制的方式废了神宗新法。
只是那样的话,就要让后宫干政,这无疑又违背《皇明祖训》,何况文官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喜欢后宫干政,尤其是当今太后张氏的子弟并不贤,在弘治正德两朝早已声名狼藉、恶迹昭彰。
所以,杨廷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请旨选宗室子为正德皇嗣的。
他更愿意让新天子只继承孝宗皇帝弘治之嗣,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承大位。
这样的话,新天子就在道义上有必要遵从孝宗之制,而可以无压力的改正德之制。
而保守文臣们素来更喜欢的就是孝宗之制。
那是一个几乎可以与两宋媲美,把士大夫抬到很高地位的时代。
不像正德朝,不但常常出现文官被廷杖的情况,还被要求脱光了打,可以说让文官尊严地位下降严重。
因而文官们做梦都想新天子重现弘治之政。
当然。
不想让正德立皇嗣,不想新天子继承的是正德之嗣的人,不只杨廷和一人。
许多文臣都和杨廷和一样的想法。
所以,除了中下层里,心思还比较单纯,或者对正德之制还比较赞同的一些文官们,还在积极劝正德立嗣外,内阁掌权的大学士和六部的主要几个尚书,现在都跟杨廷和一样,想让正德绝嗣。
哪怕杨廷和还是正德素来很敬重的老师。
但政治素来没有私情可讲。
至少对于杨廷和而言是这样的。
他和正德的那点师生之情,与他想恢复文官地位、废正德朝政制的决心,无法相提并论。
正因为杨廷和等是此想法,所以他和他的同党们,更希望的是让轮序上更有说服力的朱厚熜即位,即兴世子,正德从弟,而且继承孝宗之嗣,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承大位。
但杨廷和还是担心朱厚熜在当皇帝后会不会真的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贤君。
要知道,正德即位之初也是很仁厚的。
而杨廷和这些文官也着实被正德整怕了!
很怕新天子又是第二个正德。
尽管杨廷和这些年听闻过朱厚熜是一个宽仁好学的王世子。
为了让自己更放心,杨廷和也就还是在上个月正德突然病重连续数日不朝后,写信给自己在湖广任按察副使的学生王綖,让其再探探朱厚熜的秉性。
不过,因为文官素来不是铁板一块。
再加上,杨廷和这些人又不能明着对外承认说想让正德绝嗣,不准所有人再建言正德立嗣,而且正德的病情的确越来越重,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驾崩,所以,上奏请正德立嗣的文官是越来越多,杨廷和和他的内阁同僚们,自然也不能把这些奏疏压太久。
杨廷和自己此时也就心急如焚,恨不得王綖能够早日给他回信,让他最后再确认一下朱厚熜是不是适合做下一任天子。
而在接下来几日,的确陆续又有御史王琳、主事陆澄、陈器等文官上奏请立皇嗣。
杨廷和因而更加气愤,恨不得把这些没事瞎逼逼的愚蠢文官贬黜出京,同时他也更加焦急。
好在十来日后,王綖的回信还是来了。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杨廷和在看了信后,就因为信中的内容,而不由得神情松弛下来,且眉梢微扬,而来到内阁值房,对同僚兼好友蒋冕笑着说:
“圣天子已出矣!”
https://www.bok360.cc/book/1892430578383953920.html